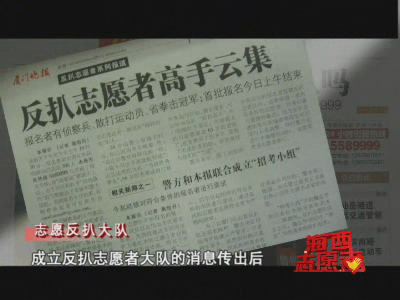(四)
凡是跟吳冠中接觸的人都會強烈地感覺到,他的血液里有一種特殊的東西,叫做“不安寧粒子”,只要一經(jīng)“藝術(shù)”的導(dǎo)火索點燃,馬上就會沸騰起來。用他自己的話說,“像含羞草,一碰就哆嗦。”
他當了一輩子美術(shù)教師,從第一天做助教開始,直到耄耋之年的最后一次登臺,其特色始終沒有變,這就是,一上講臺就激動,越講越興奮,就像陷在戀愛中,不能自拔。
其他,只要一涉及“藝術(shù)”,他馬上就變成奮起的雄獅,談話也激動,寫文章也激動,更不用說畫畫了。多少年養(yǎng)成的習慣一直持續(xù)了一輩子,他作畫,往往早餐后即開始,一直畫到下午、傍晚、深夜,其間不間歇,不休息,也不吃飯喝水,何時畫完何時才回到“人間煙火”。藝術(shù)是他永遠的新娘,初戀的狂熱一直持續(xù)到黃昏戀,始終戀不夠。
我曾問過他:“您還記得這一生畫過多少作品了嗎?”
吳先生愣了一下,連連搖手:“哦,那記不清了,太多了!2000幅總有了,也許3000幅以上?不知道了,不知道了!”
我又問:“那您的作品,每一幅,您都記得嗎?”
“當然記得。”這回他立即果決道:“每一幅都清清楚楚。因為都不是隨便畫的,我從來是有了想法才畫,否則不畫。再說,它們都是自己的孩子,走得再遠,做父母的也不會不認得。”
91個春秋飛渡,吳冠中早就做成了國際知名的大畫家,他已在北京中國美術(shù)館、香港藝術(shù)館、大英博物館、巴黎塞紐齊博物館、美國底特律博物館等處舉辦個展數(shù)十次,還獲得了法國文化部最高藝術(shù)勛位,被選為法蘭西藝術(shù)院院士等等。但他認為,做成“家”不是目的,做成“大家”也不是人生理想。
他永遠也忘不了當年留學(xué)歐洲時碰到的一件事:那天,他坐在倫敦紅色的雙層公共汽車上,待售票員來售票時,他將一枚硬幣交給她。這時旁邊的一位英國“紳士”遞過一張紙幣買票,售票員順手將吳冠中剛才交給她的那枚硬幣遞給他,誰知那位“紳士”大怒,拒絕接受這枚中國人拿過的硬幣,非要售票員重新另取一枚硬幣給他……這侮辱性的一幕像尖刀一樣插在吳冠中心上,淌著血,一直記憶到今天。國家不強大,就要受人欺侮;個人沒本事,就要受人輕慢;我古老的祖國啊,什么是你最正確、最迅捷的發(fā)展之路呢?
吳冠中將思考埋在心底:過去世界看不起中國,中國自己陳陳相因的傳統(tǒng)審美,又的確狹隘,讓人看不起。他憋著一口氣,一定要“拿來”,借鑒,改造,創(chuàng)新,不用傳統(tǒng)筆墨,畫出傳統(tǒng)精神,重新光大燦爛的東方文化,讓全世界真正認識到她的價值——這是他創(chuàng)作的思想底線,也是他一輩子孜孜矻矻、始終不渝的藝術(shù)長征。不了解他的人看他整天寫寫畫畫,涂涂抹抹,一輩子和顏料、色彩打交道,殊不知,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只為藝術(shù)而藝術(shù)的“技術(shù)主義”的畫匠。他的眼睛緊密關(guān)注著時代的進程,思考從未停止過。他說:
“畫家走到藝術(shù)家的很少,大部分是畫匠,可以發(fā)表作品,為了名利,忙于生存,已經(jīng)不做學(xué)問了,像大家那樣下苦功夫的人越來越少。整個社會都浮躁,刊物、報紙、書籍,打開看看,面目皆是浮躁;畫廊濟濟,展覽密集,與其說這是文化繁榮,實質(zhì)是為爭飯碗而標新立異,嘩眾唬人,與有感而發(fā)的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之樸素心靈不可同日而語。藝術(shù)發(fā)自心靈與靈感,心靈與靈感無處買賣,藝術(shù)家本無職業(yè)。”晚年的吳冠中還透露了一個秘密:上世紀40年代末他赴法國留學(xué)時,本是抱定“不打算回國了”的想法,因為當時在國內(nèi)搞美術(shù)毫無出路可言。但在巴黎呆久了,他越來越覺得那燈紅酒綠、“畫人制造歡樂”的社會與自己不相干。“祖國的苦難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!”于是,他終于下定了決心:“無論被驅(qū)在祖國的哪一角落,我將愛惜那卑微的一份,步步真誠地做……”
很自然的,人們會問:“如果吳冠中當年留在法國,會怎么樣?”還有研究者想知道,吳冠中對自己的一生——道路、選擇、成就、身前身后名等等,有著怎么的自我評價?
歷史是不能“如果”的。吳冠中也不是一個耽于昨天的人。他甚至說過:“明年怎么樣?順其自然。”這意思是說,藝海無涯,長征無盡頭,個人只管一心一意地探索下去,其他都無須計較——是非曲直,功勞功績,由別人去說吧。
他是藝術(shù)的赤子。他的心中只有藝術(shù),裝不下別的了。
——“天意從來高難問”。但我想來,天堂的藝術(shù)殿堂是更廣闊更明亮的,吳先生,您的第二度藝術(shù)生命又開始了,祝您縱情馳騁,續(xù)寫輝煌!(記者 韓小蕙)
 |
責任編輯:金婷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