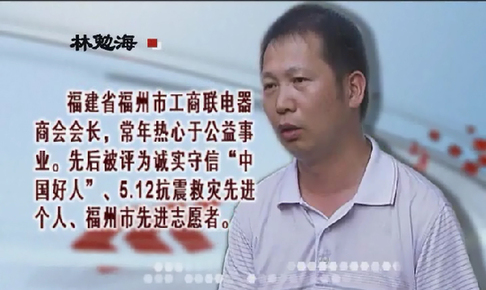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時17分左右,廣東佛山兩歲的王悅在離家100多米的巷子里玩耍,一輛迎面駛來的面包車猛然加速,將她撞倒卷到車底,右側車輪從悅悅胯部碾過。司機停了一下車,加大油門開走了,后輪再次從悅悅身上碾過。又一輛小型貨柜車開了過來,從她雙腿上碾過。慘相之下,過往的18位路人無一施以援手。由于顱腦重度損傷,10月21日,小悅悅離世。對這一事件,人們除了從道德和法律的角度加以剖析外,心理專家也從社會心理層面作出了分析。
在小悅悅事件中,18位目擊車禍者面對孩子的殘狀無動于衷,當下社會類似的看客事件似乎并不鮮見:病人在醫院內上吊自殺,值班醫生看見卻不予施救;面對欲跳樓輕生者,圍觀人群不但不予施救,反而大[中國婦女報]呼快跳;面對躺在血泊中的車禍受害者,人們連撥打個110、120電話都不打……心理專家指出,“旁觀者效應”和“發達社會冷漠癥”成為悲劇釀成的心理基礎。
“旁觀者效應”支配下的見死不救
“旁觀者效應”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現象,指的是人們見到處于危難中的受害者后,不提供任何幫助,尤其是還有其他人在場的時候。人數越多,每個人出手相救的可能性就越低,因為每個旁觀者注意到事件的可能性越低,把事件當回事的可能性也越低,就越不會感到有義務采取行動。
心理學上的“旁觀者效應”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約翰-達利和比博-拉塔內提出,源自于1964年紐約的克尤公園發生的一起謀殺案。1964年3月13日清晨,美國紐約28歲女子吉娣-格羅維斯下班回家,在路上遭到一個連環強奸殺人犯持刀襲擊。襲擊過程持續了一個半小時,其間格羅維斯尖聲慘叫,大呼救命,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,兇徒于是逃離現場。10分鐘后兇徒折返再次行兇,并實施了強奸,最后把她捅死。據報道,周圍一共有38人目睹了兇案,但卻沒有人去救,也沒有人報警。該事件震動了美國社會。
格羅維斯遇害事件促使社會心理學家約翰-達利和比博-拉塔內對旁觀者現象進行研究。他們在12年內進行了一系列心理學實驗,模擬了危急事件的發生后,結果發現:有其他人在場,就會阻礙人們出手相救。這源于一種旁觀者效應。旁觀者之所以無動于衷,是因為他們都在等待別人出手。
達利將這種現象定義為“責任擴散”。即當只有一個旁觀者時,他會意識到他負有100%的救濟責任,這種心理責任感會促使他立刻采取相應的行動,至少會去報警。但是,當有100個旁觀者時,他所負的責任就只有1%,其所承擔的心理救濟責任就大大減少。
社會心理學家認為,旁觀者袖手旁觀有以下原因:首先,在危急事件中,旁觀者面對的可能是模棱兩可的情景,影響了其決策。如果他們清楚受害者很危險,需要幫忙,就會感到有責任施以援手,否則就會觀察其他人的反應,看看別人會不會出手。如果其他人此刻也同樣在觀望,結果人人都得出一個結論:別人都無動于衷,沒必要幫。其次,旁觀者對救人有各種各樣的擔心。很多人以為,危急關頭見義勇為的人一定是陽剛十足的人,但研究發現,性格剛毅的人,例如大男子主義者,反而不愿意幫忙,因為他們害怕判斷錯誤出洋相,自己丟不起這個臉。除了出洋相,旁觀者還擔心自己水平不夠,會幫倒忙,,甚至給受害者增加危險,要承擔法律責任。
“發達社會冷漠癥”導致道德缺失
心理專家認為,小悅悅事件的發生也與國人中蔓延的所謂“發達社會冷漠癥”有關。社會心理專家岳曉東認為,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,中國人越來越患上了“發達社會冷漠癥”,它突出表現為:社會越發達,人的競爭意識越強,法律的自我保護意識也越高。由此,人們的關愛意識大幅降低,導致人情淡漠,見死不救。對此,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郭梓林解釋是,冷漠行為的蔓延,并不是人們的道德水準下降了,而是現代科技解構了原來的熟人社會,人們更多地置身于陌生人組成的社會中,原來熟人之間形成的那種“互救互助互信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”的約束氛圍也就不再具有約束力量,見死不救不再有以前熟人社會那種后果。
廣州市向日葵心理咨詢中心創辦人胡慎之認為,冷漠是“旁觀者效應”“好心無好報”的心理在作祟。胡慎之認為,此事也說明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不高。此外,這么多人選擇沉默也與一些社會上“救人者反被冤枉”的風氣有關。胡慎之覺得,正是越來越多助人為樂的事情得不到應有的尊重,才造成了這么多“見死不救”的案例出現。
改變冷漠,尊重生命,呼喚人性回歸
在小悅悅事件中,18個路人不約而同的見死不救,在譴責他人的同時,我們每個人是否都應該捫心自問——如果當時是我走過鮮血淋漓、慘不忍睹的小悅悅身旁,我會怎么做?我們怎樣才能走出事不關己、高高掛起的“旁觀者效應”的誤區和改變冷漠的心態。
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梅利莎-伯克利博士提出兩條建議:
一、如果你是旁觀者,發現情況模棱兩可,一定要忍住觀望別人的本能沖動。如果你認為有人可能需要幫助,就應果斷采取行動,畢竟出洋相只會窘幾分鐘,而你的行動或許可以救人一命。如果現場還有其他人,你要意識到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推卸責任,只要意識到這一點,你就會擔起責任。當需要發動更多的人一起幫忙時,你要指定具體的一個人上去救人,另外一個人打電話報警-,具體的指定會打消人們推卸責任的心理。
二、如果你不幸成了受害者,需要別人的幫忙,一定要讓周圍的人明確知道這是危急狀況。你要主動讓旁觀者中的一個人感到有責任幫你渡過難關——在一大群看客圍觀之下,我們以為大聲求救肯定會有人出手,但正確的做法是死死盯住一個人,向著他懇求,告訴他你需要幫忙。這會讓他突然感到幫你是責無旁貸的,而且會帶動其他人幫忙。
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顧曉明建議,將“生死教育”納入義務教育體系,讓人們從小養成愛憐生命的意識。
顧曉明認為,隨著社會生活復雜性、不確定性的增加,生死事件經常發生,人們對生死已經司空見慣甚至冷漠,對生命也變得不敬畏。就小悅悅被碾壓、十幾人袖手旁觀這一事件,足見這些人對生命的冷漠,連救人的本能良知都喪失。另一方面,看到別人不幫忙,自己也不上前幫忙,這種“圍觀心理”往往非常可怕。
顧曉明強調,要扶起跌倒的道德,有必要立法來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。自掃門前雪,可以暫時明哲保身,這也許造就了冷漠的人們。國人從不缺少俠義精神,但如果農夫總是遇到蛇,還有多少人愿意當農夫呢?在南京“彭宇案”、鄭州“李凱強案”、天津“許云鶴案”逐漸顯現“蝴蝶效應”的背景下,許多人正在遺忘道德的自覺,正在離棄對人性和良知的堅守。(本報記者 彭蕓)
 |
 |
責任編輯:金婷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