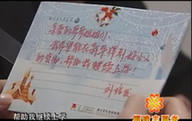“兩會”期間,作為縣直某部門一把手的趙先進(化名)去北京招商引資。40歲的趙先進坦言自己不喜歡喝酒,還是喜歡吃老婆做的酸辣土豆絲和陪女兒看電視,可喝酒已成了官場關系的一種潤滑劑,不喝就顯不出“誠意”。 經過十多年的鍛煉,趙先進現在能喝半斤白酒。在北京的幾天,他肚子里每天要灌進去5斤酒。他說“有時明知道是假茅臺還是要喝”,他甚至將自己升遷太慢歸結為自己的酒量不夠大。(3月20日 《齊魯晚報》)
本非酒徒,入了仕途,便也要整日推杯換盞。趙先進的故事,是對“一入仕途,便成酒徒”的生動詮釋。喜歡吃老婆做的家常菜,喜歡飯后陪女兒看電視,這種寧靜祥和的人倫之樂,本不是什么奢求。可對“一入仕途,身不由己”的趙而言,已然成了喧囂酒肆之外的一種可望不可即的事情。
官場喝酒成風,愈演愈烈。民眾吐槽,中央下令,三公消費裹著茅臺佳釀,依然打著接風洗塵的名義慨然秀著身姿。小酌怡情,痛飲傷身,道理不玄奧。身處酒風漩渦之中,官場人如趙先進不善、不喜飲酒者不在少數。可體檢報告上的“三高”紅燈、醫生的鄭重提醒,仍無法阻止他們“酣戰”于連臺酒席之間。吊詭的矛盾讓人“哀之又恨之”。
喝酒有諸多“不好”,肝膽心腎皆可能因其受損,毗連的應酬更是會令人心累神乏。可喝酒確有一大“好”,此種晶瑩的液體可活絡關系,疏通梗阻。不熟的人熟了,不好辦的事好辦了,認識自己的領導更多了。一口悶下,任憑腹中翻江倒海,卻博得了領導的笑顏,混了眼熟,咬咬牙便覺得“值了”。
終于,抱怨歸抱怨,真到了酒桌照喝不誤。這叫“酒肉穿腸過,仕途就此開”,如何割舍得下?以致景象百般慘烈,惹局外人惻隱。有人喝酒救駕,一命嗚呼,成了“酒烈士”;有人左手拿藥,右手頻頻舉杯,誠意拳拳;有人不顧心臟疾患,酒摻著救心丸一并灌下,視死如歸。
踩著“將自己往死里灌,讓別人說去吧”的痛苦青云,官場中的一些“偽酒徒”有幸平步上升。昔日為博上峰一點頭,爭著敬酒的苦澀也跟著涌向心頭。今日下屬向自己碰杯時,也對對方是否有“一口悶”的誠意十分介懷。忘了曾經亦是“逼不得已”,顏色頓變之間,就讓那種“非多喝不成敬意”的教條,烙印在初入仕途的年輕人心中。
己所不欲的,卻是融入官群必需的,所以不但要“施于己”還要“施于人”。悖謬沒有那么可怕,可怕的是悖謬成了無可逃離的慣性,每個剛踏入“官的場域”的人就被它的磁力緊箍。“酒鏈”由是永遠因循下去。趙先進的自倒苦水,口口聲聲說“本不喜歡喝酒”,就顯得可笑。倘若“不喜飲酒”是真的,忤逆內心意愿為了“爭寵”而把自己醉得生不如死,又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呢?倘若“告白”是假的,或者說,由當初的“不喝”到現在變得也開始享受被人“猛敬”,埋怨除了渲染矯情外,又有什么意義呢?
因此,不難理解,為何在說了一簍子“官場酒風”的壞話之后,趙先進會話鋒突變。他把自己升遷太慢歸結為自己酒量不夠大。看來,客觀原因總可以提百條萬條,主觀的攀附和放縱,總會無意識地自我淡化。一番“怪自己酒量不濟”的大表白,才算是揭示了“酒風蔚然”背后隱藏甚深的“心魔”。官場酒筵上只有兩種人,敬酒的人和渴望被眾人敬酒而不得的人。
“逼不得已的酒徒”是自欺又欺公眾的“裝可憐”。得了便宜又賣“委屈”。那些自稱“逼不得已”的官場酒徒,只不過是“紅頂誘惑”之下,他們不自覺的人格分裂式的自辯而已。
 |
 |
責任編輯:李琰之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