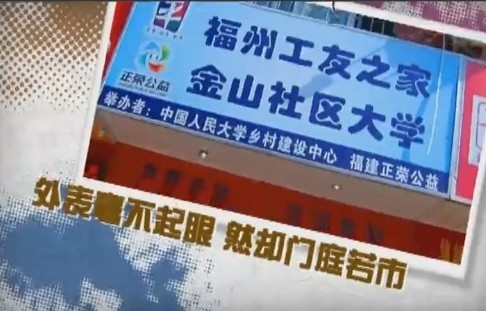文/瑜兒
深夜,時空迷離又幽靜,無數雙合攏的眼睛,同樣的沉浸入夢。
我醒著。
這種感覺很特別,有些恍惚,也有隱隱的興奮,仿佛這天地都如我的一般,沒有了束縛沒有責備沒有需要我去努力和勞累的,夜很靜,所有的靈魂都在休息。我如一個雀躍的孩子,勉強壓抑著自己,盡量端莊的坐著。一顆早已滄桑的心,即使還留有幾分純真,又如何真的能像個孩子般任性,你說是不?
好在,我已經理智慣了。
窗外無風,樹的輪廓隱入了黑幕,我在記憶里描繪著它的姿勢,回想著,它是如何萌芽如何蔥蘢,如何枯黃又如何調零。我能,我的記憶超強,即使幾十年前的一棵樹,一株草,一朵花,我仍能清晰地想起它們當年的模樣。我是跟著它們長大的,一起經歷了歲月,經歷了煙火。彼此深愛也彼此熟悉。
夜太安靜,我無可避免地陷入了回憶之中……
從小,我就對樹有著特別的感情,家鄉(xiāng)八百里秦川,一望無際的大平原。除了高高矮矮的房屋,最突出的就是那些或粗或細,或野生或家種,或蔥蘢蓬勃或初萌拔節(jié)的樹木們。
至今仍記得,童年的家門前長滿了樹木,挺秀的白椿,粗糲的洋槐,青槐,最特別的就是路邊那兩棵白楊,雙生姐妹一般一邊一個,都有一人抱粗,筆直沖天。
是的,筆直沖天,當年的我最多六歲摸樣,當父親綁好那個高高的秋千,粗粗的麻繩從高處一直垂落,我抱著母親的搓衣板不知所措的站著。父親呵斥我:去,把屋里最長的凳子搬來,搓衣板那么小,怎么成!姐姐麻利的搬來了長凳,父親一只手就把凳子舉了起來,架在了分開的麻繩上,凳子腿安全的勾住了麻繩。父親按了按,又搖了搖。示意可以玩了。一旁早已等急的姐弟爭先恐后擠了上去。父親叫我也上去,因為樹夠高,繩子夠粗夠長凳子夠寬。四個孩子,根本不成問題。我搖搖頭,一直往后退。那么高的秋千,我從來沒有見過。我害怕。秋千蕩起來的時候,村邊一溜的孩子們都跑來看。父親綁得特結實,推得手勁也恰到好處,蕩起的秋千和著姐弟們的笑聲,仿佛一直飄到了藍天上。
 |
 |
責任編輯:金婷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