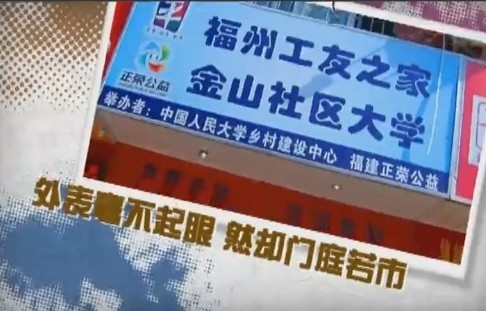秋千下的孩子們,眼睛里的光都是羨慕的。除了我。因為我的膽小,始終不肯上去,所以父親只好在旁邊的小樹上,給我綁了個小的,我的搓衣板放在上面,剛剛好。沒有人幫我推,我就一個人坐在上面,握緊繩子,退后,再雙腳騰空伸平,這時,我的小秋千就開始晃蕩,我很自得,玩得很高興,只是,我的眼光時常飄向大秋千,在姐弟們都吃飯去的時候,我負責看板凳。這個時候的我,總有一種爬上去的欲望。
記得那天的很藍,云飄來飄去的。我坐在我的搓衣板上仰望。云是一小朵一小朵的白潤,就像母親彈好的新棉。我就在想,云朵一定好暖,扯下來不知可不可以做棉衣。于是我踩著凳子爬上了大秋千。剛小心翼翼的站起來,忽然秋天猛烈的搖晃了。我已經忘記了當年,是誰惡作劇推動了秋千,只記得我從上面重重的摔了下來,摔得鼻青臉腫眼冒金星,半天都沒爬起來。父親聞聲趕來,憤怒的他直接就把凳子扔了老遠,繩索解開了,再也沒被綁上去。沒人敢抗議,父親在我們四個孩子面前,有著絕對的權威。
那兩棵白楊樹,在不久后就被砍伐了,倒下的樹身很長,直直的伸到了家門口的田地里。父親一言不發的剁著枝干,我頂著雞窩頭折一些細小的枝葉拿去喂小羊,父親讓我去數那些年輪,原來這兩棵樹,是父親小時候栽下的,父親還正值壯年,白楊樹卻已走到盡頭。父親瞪著眼看我還未消腫的臉,我看見他黑著臉眉心迅速聚攏,這是父親發火的前兆,我趕緊跳起來,抱著樹枝就跑。轉頭一看,父親卻早已彎腰干活去了。
白楊樹后來被截成了幾節,粗壯筆直的樹身被父親小心地摞起,等著歲月自動把它晾干。
一年后,父母親就開始收拾東西,最后帶著我們四個孩子和一口水缸,從老屋搬出,搬到了村南最荒涼的角落,那里,三間廈子房已經蓋起,我們徹底被從大屋分離。住進新屋不久,父親就領著我們姐弟,在院子和門前,栽下了四棵桐樹。多年以后,四棵桐樹也已長得粗壯筆直,張開的枝椏密密疊疊,整個院落門前,都是一片綠蔭。
前幾天回娘家,偶然跟母親提說這幾棵楊樹,母親笑說,問你爸去。父親蹲在院子想了半天才說,哦,那不是!父親的手指著舊屋:做了大梁了!我穿過平整的院子,走進舊屋,自從家里蓋了新房,舊屋已經成為放雜物的地方,平時也只有父母親找個舊物件才會進入。我抬頭望去,舊屋也仿佛滄桑了,大梁結實的懸在空中,支持著老屋的骨架,幾掛蛛絲爬在上面,我安靜得看它,它也安靜得看我,一晃就是三十年,它,還認得我嗎?
“英兒,好好干活,這幾棵桐樹,到時候爸伐了給你做嫁妝!”
這是我十八歲那年,第一次有人上門給我提親后,父親站在家門口的桐樹底下跟我說過的話。父親說這話時是背對著我的,他的表情我看不到,我站在他身后看他,父親仰著頭,很專注得看著這幾棵大桐樹。桐樹一溜三棵,并排栽在家門口,一樣的粗壯,一樣的筆直,一樣的青綠。可是父親的頭上,卻開始有絲絲的白發了。
父親是個老木匠,對樹有著異乎尋常的感情,從我還很小的時候,我就看著父親伐樹,解板,端詳,推磨光滑,然后再一件件的組合,一塊塊木板被父親的巧手組合成桌子椅子,小的邊角料也沒有浪費,父親把他們訂成一個個極小的板凳,于是我們家,圍桌吃飯時候坐的是高高低低。十幾個小板凳,沒有一個是一模一樣的。
 |
 |
責任編輯:金婷 |